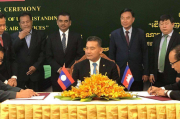本篇文章5077字,读完约13分钟
鲁元学者scholar文|鲁枢轴元、作家、文学评论家作者允许发表的那天傍晚,楼下棕榈树的影子稀疏地映在阳台上时,一个电话决定了我下半场的下落:听说你打算调动工作,不想来苏州? 电话是从苏州大学文学院打来的 我对苏州大学了解不多,“苏州”让我感动 周后,我决定调到苏州大学 那时正好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苏州大学文学院请范培松教授在会上与我面谈 范教授说我老了 当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五十多岁,作为引进的“人才”确实很老了 苏州大学从哪里知道我要调动工作? 后来得知华东师范大学的夏中义哥告诉了苏州大学文艺理论教室的刘锋杰教授。 那时华东师大徐中玉、钱谷融的几位老先生一直把我动员到上海,任命文学院院长齐森华先生和副院长飞往海口做我的工作。 尽管我与华师三代学者有着非浅的友谊,但我天生害怕大城市,所以没有激流前进的信心,终于拒绝了上海,其中具体联系的是中义哥。 徐中玉,钱谷融两位老师和常熟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来过苏州。 我好像住在面对拙政园附近街道的小客厅里。 记忆中拙政园前静悄悄的,临河家外与鳞状相比,都是粉墙黛瓦,河水在房间后面流过,女性在河边洗米洗菜,小船从河心划过,河水皱眉头在石条堆积的岸边。 在我的印象中,观前街和现在的著门横街一样热闹,但很窄。 我在旧城市开封市的井里长大。 江南苏州在我心中留下了舒适亲切的印象。 说到与江苏省的缘分,80年代初,我最先混进文坛,在上海参加笔会时,和江苏省的作家张弦住在一起。 电影《被爱遗忘的角落》博得人心,作为编剧张弦正春风很擅长。 我最喜欢张弦小说温柔悲伤的风格,经常和他聊天到深夜。 分手后又写了一点信,大部分是我告诉他创作心理方面的难题,他总是认真回复。 另一位江苏作家高晓声,当时是我在教室里喜闻乐见的江苏作家,殊不知他们在90年代相继去世了。 80年代和作家张弦、冯骡才在舟山鉴于对江苏、苏州的许多好印象,2002年春,我在位于阿姨东北角的这所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说上了年纪,但好像还是壮烈的心情。 告别海南岛时,写着类似的七律。 我记得最后两句是“去这个东吴烟波很晚,点了夕云,河里红了”。 其实我敢在哪里烧河,只是晚上吹口哨,给了自己勇气。 说引进人才,向苏大人事处报告时,工资一下子下降了2级。 人事处的劳资科长说近年来教师工资晋升的等级按规定适用。 既然想去这所学校,入乡随俗而已 幸好苏州的房价比现在低得多,小区的新花园房子只有两千元多一平方米,补助金那时的安家费几乎可以买一所房子 来苏州不久,海南的朋友还在担心我 韩少功利用来苏州学习的机会,来现代大街的新家看望,带湖北大作家方方先生来了。 方对我家的阁楼感兴趣,可能是想了契诃夫的小说 作家和苏州新家做了一点工作后几天,我在会议室开会。 接到北京的电话,是王蒙先生。 他说,听少工作你家很大,人就你一个人。 他对陆文夫也说枢元来苏州了 碰巧《光明日报》的韩小蕙来苏州了,顺便和她一起去看望陆家。 文夫身体虚弱,呼吸有点困难,但我和小蕙还说了很多话。 我跟老师说了。 我已经不年轻了。 学问的根器也很浅,以前也热闹过。 我来苏州后想静下心来多读书。 我不想参加社会活动 文夫说,他也很少参加中国的协同活动 那次相遇之后不久,陆文夫先生就去世了。 追悼会上站在我身边的王安忆,她的父亲前年也去世了。 她现在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 我觉得用这样的话表达了陆文夫对死亡的悲伤 我读过陆文夫去世后出版的文集,他在告别世界前几天还在写。 在文学人生的旅途中,他是“纤夫”,是纯粹辛苦的“纤夫” 探病的陆文夫钱谷融听说我在苏州放了新家,说要来玩两天,住在我的新家。 殷国明哥哥陪着老人来,拖着保罗箱,箱子里有茅台酒和竹骨做的旧麻将牌。 很遗憾,我不会打麻将。 我刚来没朋友,所以桌子不够 老人有点失望,我和他一起逛金鸡湖边,看见湖边有大人和孩子放风筝,老人来了感兴趣,追着天上的风筝,湖风很大,一回家就好像感冒了。 那时文学院正在申报一级学科,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晚上,学院通知吉林大学刘中树教授,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要求我陪同。 钱先生知道后也想热闹一下,我咨询了当时医院的领导,领导说人很多,安排不了座位。 钱先生说把它拿来啊。 难道中树听说钱先生在苏州,马上离开座位去我家看望! 结果,在酒席上从最初到最后都是以金谷金融为中心的话题! 钱先生那次苏州之行,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遗憾。 多年过去了,钱先生快一百岁的时候,我去华东师大二村看望他,他又说:“枢元,我还有你那里的麻将牌! 苏州大学文学院一级学科顺利批准,学校举办庆祝会,我也成了“功臣”,被授予巴掌大红书。 只有荣誉,没有奖金 最初的几年不能说是“晚霞云”,但生活很轻松 我给本科生上课,讲文艺心理学、生态批评的主题,学生们集中精力上课,积极认真地做作业 在作业中,我发现一个学生的复印件很有知识和才能。 碰巧当时院长罗时进教授来到我房间,他听了也很兴奋,让我们写下这个学生的名字,看其中一个。 结果,两人写了同名的《黄晓丹》。 晓丹本科毕业后,在苏大读硕士,然后上了南开大学,在叶嘉莹的门下读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教书。 赶上80年代,我有时觉得她可能早就成为学术的大家了。 另一名本科生徐燕被选为“保送”读研,她想和我学习,对班主任提出了要求 班主任朱老师喜欢孩子,但很严厉,批评她:你想学的人和谁在一起? 于是她多次去我上课的教室门口等着,痴情感动了 学习了三年,证明她确实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复印上下的功夫曾经被太老师钱谷融称赞过。 由于种种原因,她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中学教师 在我的价值观中,优秀的中学教师比在大学生活的平凡教授绝对宝贵,对社会的贡献也在增加。 刚来苏大几年,赶上研究生扩招,一时,我身边聚集了一群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两个复旦和清华毕业的博士课程后前来的青年学者。 我自觉学问浅,不够见习,只能真诚待人,课余,晚春早秋,和学生们一起爬花山,天平山,游灵岩寺,重元寺,山光水色,春花秋草之间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这也许还是到圣先师孔夫子的方法:浴乎县,咏归 这样的活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不同时期的其他学生们可以彼此亲近 有些老学生已经成为了有名的教授,当了大学院长、校长,尽管和刚入学的学生年龄有年龄上的差距,但还是能成为知心朋友。 我发现学生们之间的相互熏陶、相互感染比我的教育指导更有效 我在海南大学时代建立的“精神生态研究所”、创立的“精神生态研究通信”,转入苏大改组为“生态批评研究中心”,继续编辑《通信》。 2006年秋天,我们教室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海学林出版社合作,结合《人与自然》、《生态批评空间》两本新书的发表,在海南举办了生态文学研讨会。 学术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如馀谋昌、曾繁仁、朱立元、韩少功、多、徐敬亚、王小妮、尤西林、曾永成、王诺、张皓等应邀出席。 参加的有当时在中国生态批评界崭露头角,现在成了大器的青年学者王晓华、刘蓓、胡志红、宋丽、王茜等 我一生组织过很多学术会议,这个会议在别的方面召开,过了10多年依然很高兴。 我为会议制定的宗旨:既然是生态研讨会,就应该提出生态的意思 会议省建议吃节俭,全过程吃素食,尽量坐车多步行。 会场多为流动性,设置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从风景优美的海大校园一直延伸到该镇的云月湖、枳州苏东坡流淌的栾庵、礁石重叠的棋子湾、热带原始热带雨林的尖峰岭 会场的座次只有年牙不说等级。 会议论文不论形式,散文、随笔都可以编辑 当地许多“志愿者”带着车辆参加并接受服务 几十名代表上岛后的伙食费全部包括在内,不收会费,来了五天,一共消费了五万元 尽管当时海南的费用还很低,会议依然以严格的清贫精神约束着自己 棋子湾没有荒凉的酒店,所以事先给各位代表送10元,自己在昌化镇购买食物,在夕照海滩吃饭。 最初是中国傀儡诗的第一个倡导者许多老师担心有点不饿,大家开玩笑说他多年来流浪荷兰又饿又害怕! 结果,10元的自己买自助餐比在高级酒店吃得更开心 诗人多,王小妮和亿州在苏州做的另一件事是写了一本叫《陶渊明的幽灵》的书。 核心文案写作陶渊明,但写作精神并不是陶渊明式的散淡,反而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从大部分来说是为了寻找中国以前传入世界生态危机的文化治疗验证者。 他说,从小就有必要为自己多年来提倡的生态批评提供切实的例子 书,写起来很辛苦 我在《后记》里说过:“这本书的稿子,居然干了六年。” 最初完全没有推测这个选题的难度,但之后与选题密切相关的文学史研究、哲学史研究以及古代文学研究,不是我的所长,只能边补课边写 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一年后意外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当时苏州市文联主席成从武先生那里拿着花来到寒舍表示祝贺,省和市都增加了奖金,各种媒体都很热闹 这使我越来越害羞 前几天在陶渊明的家乡开会,我一生都在散淡清贫的靖节先生换成我的名利双收,真有点受不了。 苏州市文联主席成从武来到寒舍在苏州大学,满意的日子过了大约10年,是我自己的心情出了问题,还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出现了偏差,教师的时间越来越不协调,无聊得不得了。 应该填写的各种表格更多,越来越繁杂,年轻时鲁迅、胡适这些大卡教授一生填写的表格恐怕也没有我们一年的东西吧。 发表论文必须是“核心刊物”,是校方指定的几个“核心” 没有什么长篇论文是我在乐黛云编辑的有学术分量的“文化间对话”上陆续发表的 以前,我的文章经常转载在文摘类刊物上,近年来,学问自认所长比以前进步了,但提交文章的人消失了,据说这样的刊物也已经“承包”了。 因为学校死亡的退休制度,我62岁的时候就做好退休准备不再招收研究生了。 等到65岁退休,学校党政联席会协议我延期到70岁退休,还可以招研究生。 我刚招收研究生,根据学校的规定,67岁进入“准备退休”的时间段,不能再招收研究生了 这样折腾,从62岁到70岁的8年间,我只能带博士学生。 然后,受到了校方特加的恩宠。 自己想也很有趣 (听说现在规则变了。 教授只要有经费,80岁就可以带研究生)规章制度越来越严格。 而且学生的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教师学科创新的动力越来越不足。 至少我的心情是这样的。 初来苏大,我课不同学科的同学都有选择,外学院的学生也在旁听。 教室后面经常临时增加长椅,连小教室都要换成大教室 后来,以为学问盛行了,想教的学生反而大幅度减少,连文艺学科的研究生都不想做很多选择,剩下的只有我自己的几个学生,才能活着。 我体会到王元化先生临终前发出的叹息。 这个世界已经不被爱了! 而且,我年轻时的学生,现在是多产翻译家张月教授翻译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在《法令不能改变社会》( onnechangepaslasociétéPardécrit )一书中表达的思想 我们应对很多复杂情况的制度手段的性能下降,仅凭逻辑上扮演的条例规则无法说明实际的境遇。 我不能让学生改变社会,所以我只能限制自己退出这个游戏。 于是向校方申请提前退休,马上得到了批准 年国庆节后,苏州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关于教育界诸多弊端的投诉复印件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个网站上,他说:“全国有名的文学评论家鲁枢前教授也刚到60多岁,黯然离开苏州大学,回到河南省老家的大学重新就业。 ”这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和事实有很多不同,我想借本论文发表的机会明确一下:校方根据过程将退休延期到70岁,我自觉没有意思,这样混淆无疑是自作自受。 今年苏州的梅雨,即使下雨也有可能受到清风的袭击,但置身阳台的窗户下,反而很凉爽。 天渐渐晚了,别墅湖湖面上云黑水白,樟树林青葱茂盛,深绿 脑子里反而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我五岁半上小学,学校设在老寺庙里,离我家不到一英里,沿着惠济河河岸走,穿过两座板桥。 我不记得家里人送我的。 瘦小的孩子背着家里做的蓝布包,一边走一边看着漂浮在河里的鳃鱼,从草丛里飞出的蚱蜢,飞过树梢的蜻蜓。 从惠济河到独步湖,从开封到阿姨苏,70年过去了,对我来说也几乎从“北宋”变成了“南宋”。 北方喝白酒多年了,南方学会喝黄酒了 白酒浓,黄酒长 白居易诗说。 “秋风江上波无限,暮雨舟中酒是樽。 “他喝的也是黄酒,也就是古人说的“醴”、“醪”等 杜甫感叹:“酒债在普通的地方,人生七十古来稀。” 老杜只活了59岁 毕竟,我喜欢潇洒的苏东坡。 "人生如梦,木桶还酢江月. " 己亥梅雨期阿姨苏暮雨楼原标题:“鲁枢轴元:阿姨苏暮雨酒一樽”原文
标题:热门:鲁枢元:姑苏暮雨酒一樽
地址:http://www.3mta.com/xlxw/19845.html